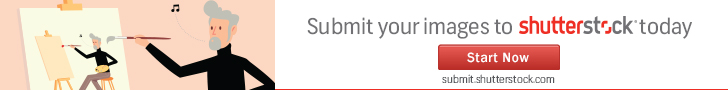六號病床前陣子來了個四十歲的男病人。 他是臥病在床十四年的漸凍人--康先生。
漸凍人在前些日子因為社會發起籌款活動,
康先生身子瘦弱, 安靜的躺在病床上。
這回康先生住院,主要原因是在護理院跌倒。
由於肺炎情況不好, 醫療團隊決定幫他裝鼻管,以避免肺炎情況惡化。
康先生住院第五天,剛好到我值班。這天他的氣色蠻好的。 他雖然無法清楚用語言表達自己,
這天早上我幫他抽血之後,手沒有放回他喜歡的位置。 他開始咿咿呀呀的。護士走上前和藹的說:「康先生,怎麼了, 一定是你的手沒放回原位對吧!我來幫你放好。」
護士把康先生的萎縮的右手放回他胸前。那是他最喜歡的姿勢。
醫生認為康先生的情況好轉,抗生素也可以開始轉換成口服抗生素,
中午十二點,探病時間開始,病患家屬陸陸續續來到病房探病。
下午一點左右,
「啊,怎麼會用嘴巴喝水呢?」我焦慮的問朱護士。
「我也不清楚,我在隔壁床喂病人吃藥,
我走到六號病床旁,語帶些許憤怒質問病人家屬。
「啊!別再傷害他了!」我心中默默感嘆。
這天就因為這樣一個餵食的小動作,康先生情況突然不好了。當然,
那天之後,康先生的病情天天惡化。原本不需要氧氣支柱, 后来换了一个比一个还大的氧气罩, 康先生病情每况愈下。
我每个早晨帮他抽血验血氧。
“康先生,会喘吗?” 我拍拍他的肩膀每两个小时问一次。 他总是瞪大眼睛看着我,然后要紧压根的样子,努力想要回答我。
康先生的反应越来越慢、越来越慢。
那天下午兩點五十,病人開始不清醒。布簾拉上,
「他準備離開了,趕快叫您們的兄弟姊妹回來陪伴吧。」
康先生離開的倉促,沒有太多疼痛。 十幾分鐘後心脏监护示波器顯示直線,康先生離開了。
在為康先生做最後檢查的時候,心中一些小漣漪。
病患的哥哥看病人已離開,沒有多問什麼,心情看起來格外平靜。
一個臥病在床的病患,活著,卻苦苦哀求家人讓他早點離世,
啊。
很多時候太多太多的人告訴我們,依據我們的上班性質,
他,終於離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