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好,我是岚医师,入行一个月,请多多指教。
现今社会,不管哪个行业都竞争,社会的哪个角色都不好当。我秉持着自己心中满满热忱,走入病房,开始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碑——当起实习医师。
曾经,我是一个多么胆小的女孩。我害怕苦难,更恐惧死亡。
在开始上班的这段日子里,我才慢慢意识到,原来生死离别,是如此平静,甚至可以不带一丝悲伤。
光先生已经在十八号病床呆了一周,这回入院的原因是肺炎。他戴着氧气罩,瘦瘦的身子,静静的坐在病床上,默默的喘气。
由于是大叶性肺炎,病人得住院观察,天天静脉注射抗生素。八十几岁的老先生,充满老人斑的双臂,处处是导管拆拆装装的伤痕。老人家的皮肤弹性不及年轻人,伤口的愈合能力也越来越差,皮下的淤血处越来越多。
每三两天,护士就会告知装置导管处红肿,需要再找新的血管装置新的导管,以定时注释静脉抗生素。
虽然处处是伤口看起来很叫人心疼,但不装导管无法注射抗生素,病人无法痊愈,更叫人忧虑.
光老先生住院的第二周,医疗团队看他情况越来越好,决定把氧气罩拿掉,改成鼻导管。这天,光老先生戴着鼻导管,一早坐在病床上,开始看起报纸来。看到病人的情况越来越好,我满心喜悦。这天他的精神看起来不错,胃口也变好。
这个早上,我为他抽血的时候,还多聊了几句。
“光先生,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哟!”我边抽血边说道。
“是啊!”他轻声的回答,微微笑的样子真慈祥。他笑起来眼睛弯弯像月亮,那个表情让我印象深刻。
在一旁的儿子说到: “是呀!他今天情况好多了,开始吃饭看报纸,就跟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一模一样!”
“好呀!希望您赶快好起来,赶快可以回家去。”我微微笑回答道。
光先生用力的点了几下头,好不开心的。
每每看到病人痊愈中,离出院的日子不远时,心中总有种小小的喜悦。
之后,我休了两天假,没到医院上班。
三天后上班的这天,我看到光先生尽然依旧躺在病房里的十八号病床。那个早上他睡得很熟。
病人不出院的原因百百种,我当天也没多问同事,心想可能只是血氧又不漂亮之类的小问题。那个早上巡房时,我才听护士说,光先生昨午后已开始昏睡,意识渐渐不清醒。后来紧急安排了一个脑部断层扫描,才发现光先生脑部缺氧性中风。
但在断层扫描之后,他又醒过来了。反反复复的,我这个实习医生每两个小时就跑到他床边去,拍拍他的肩膀,问道:“先生先生!你叫什么名字?”
重复的问题问了一边又一边,只见光先生带着氧气面罩,边喘气,边努力回答。
他,是清醒的。
看他喘得不得了,我帮他抽了好几次血,以确保血氧充足。
“光先生,我帮你抽血,看看血氧如何。会痛哟!要忍一忍,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这是我一贯的抽血前言。
当时,光先生喘得厉害,戴着氧气面罩,发出几下“呜呜”声。我困惑了,那到底是回答还是喘气的声音。
光先生年纪大了。在稍早不清醒的那个早上,专科医生已告知家人病人情况不乐观。也因此不建议插管或心肺复苏之类的急救。家人们明白病人情况,并同意医生的建议。
光先生就这样睡睡醒醒十几个小时,最后,在我值晚班的这个晚上,突然不呼吸了。
护士连忙把帘子拉上。值班的我跑也到光先生床边,拍拍他的肩膀,大声的喊道:“光先生,光先生,光先生… … ”
光先生一动也不动,没有任何回应。
耳旁只传来氧气面罩氧气不断往外流的嘶嘶声。
他已没有脉搏,没有呼吸,没有心跳。
我拿出口袋里的诊查电筒,检查了他的瞳孔——瞳孔已放大,对光无感。
当时候病房有些混乱。有氧气罩的嘶嘶声,有心脏监护示波器的嘀嘀声,还有护士和家属的说话声。
我把听诊器放在他胸口前,最后一次聆听他的心跳——在正式宣布死亡之前。
听诊器放在胸口的那刻,我听见这辈子从未听过的安静,与世隔绝的安静。这刻,死亡来的好平静,平静的让我忘了害怕和恐惧。
我把听诊器从耳朵摘下来,转过身,放空的眼神和他儿子焦急的眼神四目交接,说到:
“光先生走了。死亡时间,八月二十三号,凌晨十二点零五分。”
转身,离开。
此刻,内心世界如此冷冰。
岚 医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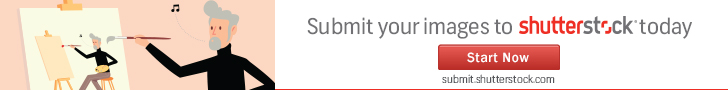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